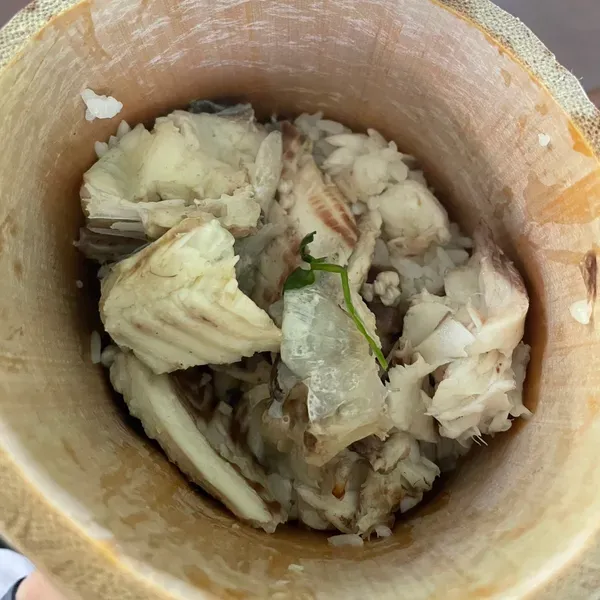這時候也再不用說什麼清不清楚,我太清楚,太感懷,我恭喜自己又再一次想起你。
我本來真以為這裡只是個騙人的死局,人被愛騙到這裡,留下愛的謊言,再由老闆來騙人到這裡,留下愛的謊言,周而復始,萬象更舊。但實際坐進來後,我才知它的本質,比起魔術師,更像販夢的。
我已沒有什麼牽掛,想掛的掛不住,欲愛的愛不了,永遠是強人所難;但你又知道,我的愛戀有時會消沉太久,有時又像現下我難堪的一張面孔掛淚,我始終妄想找到你,只恐這原是你的安排,你和我一樣,都想要這種化為灰燼、羽毛的轉瞬之慟。
反正是這樣的,當我無意間走進錄音室,一見桌上那些設備陳列,完整、美好地等待來人,我想起曾經非常喜愛的一部電影,說我同樣、慣愛的詩人,〈Il Postino〉。為了你,其實我也做過幾百回竊詩大盜,也做過情深不渝的女信差,愛你的信燒一點少一點,火與明月卻像你唇齒間那枚白球愈發皎亮;有時也為了你,我踏上脫序的軌跡,嘗試逃學,避開一切陳言的機會,而始終不知你去了哪裡?你絕對難以想像、難以負荷我是何等地想念你,和其他物質和愛情無關的,我看見阿諼也想起你,看見夢裡你手掌微微屈起,像索要一段過程。
怎會如此,我本不該。如果我傾身向收音道,順著長長的電線,它會流進你的房間,連通你的耳道嗎?如果一日再見你,想我應該不會再膽怯,應當心平氣和地握住你的手,向你介紹我的所有,那些變和未變的。
故致以為你已經逝去的我,一個短暫的生命。
24.06.11
隨記。